李晓晨篮球(旁观者清:他们这样看待异性恋的世界)
更新时间:2022-11-14 23:58:32作者按:
用一段话来总结我和这几名采访者的谈话是很困难的。
我是个直女,起初奔着“因为身份认同小众,所以应该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吧”这样的思考接触了近十位 LGBT 采访者。他们多少确实回答了我的疑问,谈到了与社会、与家人、与朋友、与恋人甚至与自己的相处和反思。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一位采访者都对谈到的其中一个问题给出了相同的回答和体会,这像一面镜子让我反观到自己身上一直以来被忽略的“直人癌”。
如果硬要说性取向让他们的人生变得多么不同,那么只能说他们的视野和认知更不受限于既定规则,除此之外与他人无异。在谈话中我时常感受到,按性取向将人草率地划分出不同类别是不合理的——他们甚至自己都不会把 LGBT 当作人生的一个标签。正如一位因为客观原因我没有写到的一位采访者描述的那样,有人喜欢粉色,有人喜欢蓝色,有人喜欢吃红烧肉,有人选择全素食。但你就能说喜欢吃红烧肉的人和素食主义者本身有多么得不同么?
这样的体会让我对于自己最初采访的既定“直人”视角感到惭愧。
“(直男)可能不会考虑到要保护自己”
黄高乐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做策划相关的工作。但说起如今“LGBT霸权”和强迫性政治正确,黄高乐一样滔滔不绝,像是在为直人喊冤。
钢铁“弯男”。黄高乐这么形容自己。他说,就像“钢铁直男”生来就知道自己完全不可能喜欢男性一样,黄高乐从幼儿园记事起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喜欢女性。老家在重视传统文化的山东烟台,黄高乐说,从幼儿园起,就有老师和亲戚开玩笑地对他讲,他长大要娶媳妇。每当这种时候,小黄高乐就有些担心。
出生在1991年,黄高乐童年时期电视台里还播着《美少女战士》和《百变小樱》这样的进口日本动画片。虽然他把《美少女战士》形容成为一部“异性恋霸权”的动漫,但他还是在里面看到了同性恋的映射。黄高乐早就不记得动画里“四大天王”都叫什么名字了,但在小学看到这部动漫的时候,发现其中两大天王(佐伊赛特和昆赛特)的对话,模糊地交代了他们的恋人关系。
“还是要感谢日本动漫。”黄高乐回忆说,“我虽然知道这种情况不多见,但我知道它是存在的。”
那会还不懂这叫做同性恋,但黄高乐明白了原来男生和男生之间也是可以有爱情的。在周围大人都默认黄高乐长大要娶妻生子的环境下,在日本动漫里看到同性恋情,帮他顺利地建立了身份认同。他说,相比那些一直无法建立自我认同的、回避自己的同性恋来讲,黄高乐从来没有因为自我的认知冲突而造成的病耻感。
黄高乐说,他初中时喜欢过一个同班的直男,也向对方表白了,有时还会一起在校园里散步,可对方却一直以为他所谓的喜欢和兄弟感情无异。直到六年后,男生高中毕业去了军队,突然认识到同性恋的存在,才对初中时黄高乐的表白恍然大悟。男生趁假期在一家肯德基约见了黄高乐,郑重表明自己不喜欢男生。这时隔六年之后迟来的拒绝让黄高乐哭笑不得。
“实际上我会为这种直男捏一把汗,你知道吗?”黄高乐说,“他可能不会考虑到要保护自己。” 因为缺乏性教育,性意识不浓烈,或是过于强调异性恋、忽视同性恋的存在,黄高乐认为这样的直男和男同性恋相处时完全没有防备。“他很有可能是暴露在一种性侵的环境下”,黄高乐说,学校极力地压制性教育的结果,最终是害了这些直男。
再比如,在滴滴顺风车因为乘客安全问题整顿业务之后,6月13日滴滴宣布夜间顺风车暂时恢复运营,但要求乘客和司机是同一性别的。这一则消息背后的逻辑,也顺应了黄高乐所指的,因为缺乏性教育和性意识,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大环境规避的是异性之间的性犯罪,但人们仍然有可能暴露在同性性犯罪的危险之中。
除了性教育外,黄高乐特别倡导 LGBT 出柜,但反对“LGBT 霸权”。一些异性恋对于同性恋平权的态度是中立的,也就是“不支持也不反对”,而一些 LGBT 人士会激进甚至带有攻击性地回应,好像逼迫这些中立的异性恋支持 LGBT。黄高乐认为,这样做法会把这些中立的主流人士推得越来越远。又或者,若直男和同性恋开玩笑问能否改变他性取向就是歧视,而同性恋却可以和直男开玩笑说将对方“掰弯”,这也是黄高乐认为的一种 LGBT “蛮横的特权”。
“为 LGBT 平权或者同志骄傲运动,必须是建立在不贬损异性恋的前提下”,黄高乐说。他认为“LGBT 霸权”者不能代表所有LGBT人群,也不是真的平权。
相反,他认为 LGBT 应该尽力出柜,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这个群体的可见度,再通过沟通和交流化解主流群体的误解。他不认为因为无知而向他询问性取向是否可以“纠正”是冒犯。他身边完全出柜的人,也只有和牵扯到中国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的家人需要努力的沟通,而同学、同事、朋友都鲜有反对的情况。他说,中国主流对待 LGBT 仍有轻视或蔑视存在,但已经远远没有歧视或者迫害了。
-
“他们对待感情太粗暴了”
一次纪念日小眼送给果果的手工立体贺卡。小眼左手上带的白色手表是果果在两人一周年纪念日时送的。
小眼初中的时候还跟着同班情窦初开的几个女生一起,共同仰慕在篮球场挥汗如雨、看起来干净阳光的高中学长们。那时小眼在班里像只小兔子,就连活泼大笑的时候都透着一股文弱的气质。因为一直在实验班努力学习,小眼早早就戴上了眼镜,高中因为外地户口不能参加北京高考而被父母带回了有些陌生的老家。用她的话说,她从小就是一个特别顺从父母的乖乖女,一直做着他们心里想要的那个女儿。
小眼从老家考取了北京一本的大学,也有了两段校园恋爱经历。大四时去支持闺蜜的校内篮球比赛,在球场上看到了果果。小眼说,当时整个人突然呆住了。她知道眼前的这个领导着整个球队的人是个假小子,但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对果果产生了触电的感觉,以至于正在打球的果果都注意到了场外小眼的眼神。
后来,果果成为了小眼的第一个女朋友。
“遇到她之前会刻意地只看男生。” 小眼说,“但现在不会刻意去用性别划分喜欢的对象。”
小眼说,以前和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不自觉地有些“性别模式”在里面。比如很自然地,有些时候,作为女生的小眼可以耍耍赖,然后男朋友也好像很理所应当地去哄好她。但在和果果谈恋爱的时候,她说,也许两个人都是女生,就没有了因为性别角色所带来的那些“理所应当”,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回想起自己曾经和男生谈过的恋爱,再看看周围大多数人的恋爱观,小眼说,“他们对待感情太粗暴了。”
果果和家里人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父亲。向父母出柜之前,果果也曾担心过父母是否能接受,但向来相信积极沟通、事在人为的她,在一次失恋之后选择向父母坦白心事。果果的父母从外地赶来北京,三个人在宾馆哭成一团。让果果感动的是,父母情绪稳定一些之后就开始安慰她,帮助她从失恋的情绪中走出来。那次失恋,对果果更大的意义是,父母接受了自己。
但果果知道父母消化这件事需要一定的时间。她说,父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去“解释”果果的性取向。她曾经听到父母吵架,父亲责怪母亲年轻时候也跟几个闺蜜关系非常好,“孩子这样还不都是你造成的”。还有一次,母亲在家里接了个电话,是亲戚家女儿的婚礼邀请。果果的母亲没说话,和站在电话旁的父亲对视了一眼,两人眼圈一下就红了。果果说,她理解,她知道那时候父母在想,他们的女儿不会有这样一个婚礼了。
这些都让果果心痛。果果的父亲一开始也带果果找心理医生看过“病”,但在这些荒谬的经历后父母接受了果果的取向。她因为父母接受真实的自己而感到幸福。果果觉得她应该让父母了解真实的自己,但父母却不该去承受那些社会环境带来的压力。果果马上要去美国加州攻读士后了,她说,要努力比别人过得更好,要让父母过得更好,来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女儿没有错。
交往了一年之后,果果提出想让小眼见一下自己的父母。小眼说,她知道果果一家人关系特别好,果果是他们掌心的“香饽饽”,也特别接受她们的感情。小眼想象着见面时,万一果果父母问起她父母的态度,自己该怎么面对。“我觉得我得给她父母一个交代,我不想让她父母觉得我在骗他们女儿的感情,或者羞于承认”,小眼说。于是,小眼鼓起勇气跟保守传统的父母出柜了。
想让父母了解真实的自己,再也不想做父母想象中的那个女儿了。小眼也担忧过向父母出柜也许会失去他们的支持,但后来便觉得这件事在于自己努力争取了多少。她比喻,出柜也像筛子一样,筛去了在她最真实最脆弱的时候不愿意支持她的人。小眼说,“如果我都这么努力了,他们还是不支持不理解,那他们原先支持的也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我啊。” 出柜这件事对于小眼来说,不只是宣布自己的取向,“是接受自己,坚持自己的选择”。
说起初中时班里小白兔的形象,小眼开玩笑说,以前是微漫画里那只小白兔,“(狗熊问)你那么干净能用你擦屁股吗?‘嗯,可以啊。’ 但现在就是,‘不不不,擦屁股不行。’” 说完小眼又笑没了眼睛。
-
“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
李晓晨将采访地点选在了南锣鼓巷旁一间小剧场的咖啡厅里。剧场活动多在下午,早上安静鲜少有人。虽然是夏天,李晓晨还是点了一杯热茶。
家里电视上放着李玉刚的节目,李晓晨的父母看了一眼便随口说,这不是变态么。李晓晨也没在意,他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同性恋什么的,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
“不过李玉刚属于性别表达,不是同性恋,”现在的李晓晨会特别注意不混淆概念,不再像以前一样把人分为“正常”和“不正常”。
从小李晓晨的父母就念叨他的阴柔,他也一度非常认同父母觉得男性就应该阳刚、强壮的观念,于是也非常努力地锻炼身体,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强撑一副男子汉的样子。“我那时候也想变成阳刚的人,但努力的过程有点难受”,李晓晨说。认识小齐之前,李晓晨向两个女孩子表白过心意,但都被拒绝了。
准备考研的阶段时,李晓晨经常去学校的图书馆自习。一次邻座的小齐向他借笔芯,在递笔芯的瞬间对视了一眼,然后李晓晨就开始心跳加速。借笔芯的纸条就这样传了下去,随后发展成为了三、四天的短暂恋情。
一次吃饭的时候,两人聊到考研目标。李晓晨发现,小齐来自于较富裕的家庭,也是通过父母关系在中国政法大学自习,觉得研究生有学上就行了。而本校的李晓晨却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法。李晓晨觉得话题对不上的两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有冲突。加上李晓晨拒绝了小齐迅速提出的更亲密的请求,隔天小齐就以不想打扰李晓晨学习的借口结束了这段感情。
在这之后李晓晨才开始冷静下来,想到了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一边是沉浸在失恋的痛苦里,于是没日没夜地埋头学习,以至于忘记了去考试的现场确认,导致失去了考研资格。另一边,李晓晨认为发现自己喜欢男生这件事像是“一个灾难”,不敢去回想,“怕引起一系列的后果”。
他觉得自己“不正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病”。“我之前也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词,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词跟自己没关系”,李晓晨说。
失恋情绪平稳了之后,李晓晨开始思考自己的另一种可能,思考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心理沙龙的活动,虽然也不清楚具体什么内容,李晓晨戴着帽子口罩“全副武装”地就去了。
李晓晨没见过同性恋。一想到同性恋,李晓晨就觉得这些人可能是“飞禽走兽”。“穿得很奇怪,习惯奇怪,各种奇怪”,李晓晨说。他觉得自己是“正常人”,觉得“心里有点抵触,害怕”,于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他说,“想先看看同性恋的人都长什么样。”
那天,全副武装的李晓晨,看到台上的其他人坦诚地分享自己的取向,李晓晨感到安慰的同时也觉得有些冲击。他说,“呀,就跟大街上看见的人一样,各种职业各种工作各种背景,跟其他人完全没有区别。” 李晓晨反思,是不是以前自己把一个人的性取向夸大了,觉得没有必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毕竟就是一个人的一部分而已”。
-
“可我也是女孩子呀”
张温柔说,这家火锅店斜对面那条街,就是她前女友和她分手的地方,到现在也没缓过来。
张温柔说,她身边的人得知她喜欢女生的时候都很惊讶。“我可能看起来不像吧”,她说。一头黑色及腰的卷发,会戴美瞳会把眼睫毛刷长,张温柔说,也许人们对女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就是那种看起来短发帅气的假小子。
也许因为看起来不像,她身边的直男朋友都觉得她喜欢女生这件事是“闹着玩”的。也有直男说,“‘你们就是不知道和男生谈恋爱的好’”,张温柔复述道,好像身边的直男朋友觉得她们“玩够了“新鲜就会变回异性恋。
直到和前女友分手,张温柔一下胖了40斤,看到她难过的样子,一名直男朋友才意识到,原来她是认真喜欢女生的。那之后,张温柔经常看到朋友转发一些为同性恋平权的文章。有点无奈,但也挺感动的,张温柔说。
张温柔身边有一群固定的朋友,周末聚会晚了就会一起在其中一个朋友家过夜。有时在她刷牙洗漱的时候,知道她是同性恋的直男朋友就会毫不避讳地推门用洗手间,这让她觉得心里很别扭。“可我也是女孩子呀”,张温柔说。
-
“无性恋是什么?”
采访约在了小包的实习机构,北京同志中心。茶几上放着一张日本媒体记者的名片。小包半抱怨地说,这个记者刚来过,问的问题很明显是有指向性的,就想听 LGBT 在中国有多受压迫。小包是香港户口,但她说精神上已经把自己户口迁到北京了,“北京太有意思了!”
“阿包啊,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是无性恋?”被自己的高中好友小林这么一问,小包开始查找无性恋的资料。
用小包的话说,在小学和初中二次元动漫盛行的时期,她发现自己对男生和女生都会产生好感,或者更准确的说,在产生好感时,小包并不会太在意对方的性别。于是她初步把自己定义成为了双性恋。后来觉得自己可能是泛性恋,再后来就被小林问到了无性恋的问题。
小包说,无性恋这个词原先是听过,但也没细想过是什么意思,于是就开始上网查资料。“知乎上‘无性恋是怎样的体验’这样的问题,下面只有三个回答”,小包说。那时网上的资料非常少,但她已经隐约发现自己也许真的属于这个世界上稀有的1%人口了。
为了进一步确认,小林带领着几个共同朋友,为小包开展了为期一年半左右的“取向探索”。他们甚至为小包联系了性工作者,还以她的名义在同性恋交友网站上创立了一个账号,最后都因为小包实在无法接受性行为而告终。
而这种玩闹一样的“探索”,让小包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取向。她发现自己可以理解性感的概念,可以分辨他人性感的瞬间,但这些瞬间却无法让她在生理上感受到性吸引。
坦白说,小包面对的最多的问题,除了无性恋是什么,就是无性恋和性冷淡的区别。小包说,她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具体区别,咨询过的医学朋友也告诉她两者没有病理差别。因为她自己的性欲低下,和性冷淡的概念有些重合,所以自己也无法解释。但性冷淡是生理没有反应,而小包认为自己是心理不想和人有亲密行为。
“所以硬要说两个哪里不一样,我就说哎呀一个可以治疗一个不可以”,小包会这样回答。
对小包来说,出柜显得容易得多。一天她打电话给妈妈,报告了近来的生活,顺便就告诉了妈妈自己是无性恋。接下来,像小包其他出柜经历一样,妈妈问道,什么是无性恋?在小包解释完之后,妈妈很波澜不惊地接受了,问道,所以你是不想结婚吗?小包觉得这样的理解虽然有些偏差,但这也确实是她会做的事情。最后妈妈劝她,可以不结婚,但最好还是要个小孩啊,陪伴很重要。
在北京同志中心实习的小包见过太多因为无法认同自己而遭受心理困扰的同性恋了,而身为比同性恋更稀有的无性恋小包却没有这样的自我厌恶。
“目前社会上针对跨性别、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污名是过于严重的,无性恋之所以还没有被波及到,是因为它太小众了,等无性恋真正的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里面,它会遭受怎样的污名化,我不知道”,小包这样说。
注:根据意愿,部分采访者使用真名,部分使用假名。
相关推荐
-
李晓晨篮球(旁观者清:他们这样看待异性恋的世界)
查看详情
-
李晓勇与加代的关系(四九城江湖录之加代篇第十二章海明出卖加代)
查看详情
-
cba篮球队员吴冠希哪里人(你知道CBA三大富二代球员吗?吴冠希迎娶张常宁,李晓旭家产过亿)
查看详情
-
2008奥运会男篮有哪些人(08男篮集训18人名单中仅易建联、周鹏、刘晓宇、李晓旭为现役球员)
查看详情
-
乒乓球亚洲杯几年一次(乒乓球亚洲杯举办了多少届,大满贯张怡宁和李晓霞竟然没夺过冠!)
查看详情
-
cba球员在哪里打比赛呢(CBA三消息:广东队悍将NBA观赛,郭艾伦踩点训练,李晓旭加练罚球)
查看详情
-
2012年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名单(伦敦奥运会女团,李晓霞丁宁郭跃合作夺金,日本银牌创历史最佳)
查看详情
-
李晓旭越剧凤凰台(越剧《凤凰台》:戏曲迎新不辞旧,新戏要老,老戏要新)
查看详情
- 最新资讯
-
- 2022-11-15 2夺欧洲杯4获世界杯(俱乐部的成就引领国家队的辉煌——世界杯巡礼之西班牙篇)
- 2022-11-15 谁能介绍韩国国国家足球队(韩国足球,在欧洲是什么水平?)
- 2022-11-15 篮球世界杯中国最多几强(支持杜峰下课,但是中国男篮从世界第八沦为亚洲第八这个锅不该背)
- 2022-11-15 奥运会分为田径和什么(数说奥运:少年强则国强)
- 2022-11-15 中国男足VS沙特男足动漫图片(这部足球动画让日本队踢进了世界杯)
- 2022-11-15 世界杯进球最多的赛事(历届世界杯决赛里面11大进球最多的比赛)
- 2022-11-15 nba2k20手游在哪个平台(《NBA 2K20》试玩版报告:更加平衡的篮球体验)
- 2022-11-15 萨拉赫升至第三位(萨拉赫离封王就差一个冠军了,创下4大里程碑纪录 梅罗之后第三人)
- 2022-11-15 世界杯阿根廷队服(世界杯开赛前9天,阿根廷做出重要决定!恭喜梅西,封神希望大增)
- 2022-11-15 切尔西正式引进科瓦契奇(切尔西历史上最贵的十笔引援,五位难说成功)
- 推荐攻略
-
-
乌克兰总统身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解除乌总检察长及国家安全局局长职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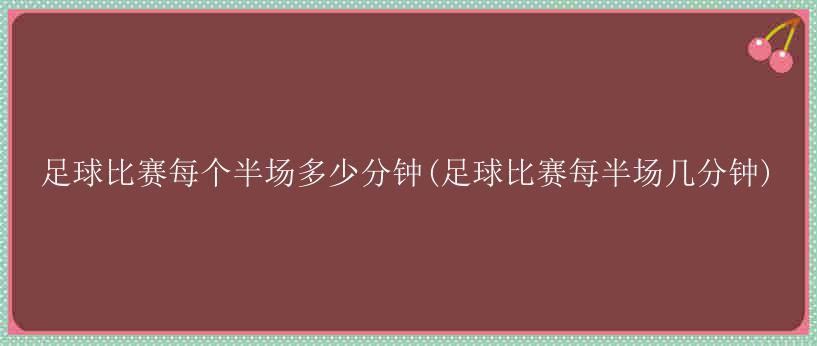
足球比赛每个半场多少分钟(足球比赛每半场几分钟)
-
2021中超今天哪里转播(今晚!中超2场对决,CCTV5 直播申花PK武汉,腾讯体育亚泰vs天津)
-
2022梅西坠机身亡事件结果(足坛变天!巴萨无缘榜首的2年:梅西告别,老马去世,2-8惨案)
-
2021全运会篮球直播赛程辽宁(4月22日央视直播:CBA总决赛;赵心童vs马奎尔,塞尔比vs颜丙涛)
-
中国最强导弹(世界洲际导弹前10排名,中国东风导弹领先美国,第一名堪称导弹王)
-
2021篮球比赛在哪里看(CCTV5直播NBA 辽篮争夺CBA总决赛冠军点 颜丙涛出战斯诺克世锦赛)
-
东航结果不敢公布了(民航局再次回应东航MU5735事故调查!查明原因有多难,多久公布?)
-


